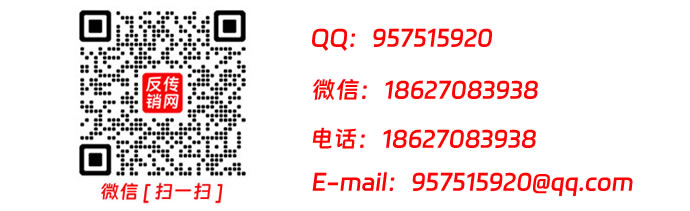增強立法針對性有效打擊網絡傳銷
合理確定立案追訴標準
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在2010年頒布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以下稱“立案追訴標準二”)第七十八條第一款確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為“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其中,“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定罪要件不甚合理。首先,該標準實際上是參考了傳銷組織的“五級三階制”組織制度(“五級”指傳銷組織內部的成員分為E、D、C、B、A五個級別;“三階”指會員晉升分三個階段:E級晉升D級、D級晉升C級同屬第一階段;C級晉升B級屬第二階段;B級晉升A級為第三個階段),將組織者、領導者確定為C級以上。此規定看似具體,實則包含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傳銷組織制度并非單一,“五級三階制”只是其中較常見的一種,而且還可能發生變化。“立案追訴標準二”將層級明確規定為定罪要件,卻未予解釋,必然導致認定犯罪是否成立上的困難。其次,將組織、領導三十人以上和層級在三級以上兩個條件同時具備作為定罪要件,可能導致某些傳銷犯罪嫌疑人由于層級的不確定而逃避刑責。綜上,建議將該標準修訂為“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或者層級在三級以上”,同時可考慮將非法獲利的數額作為定罪的選擇性條件,以增強司法認定的可操作性。
建議增設傳銷組織罪
傳銷活動積極參與者是指傳銷組織中除組織者、領導者之外的,發展下線人數較多,或多次被查處仍從事傳銷,或采用誘騙、脅迫等手段發展下線的傳銷人員。大量案件表明,傳銷活動積極參與者是傳銷組織中的骨干力量,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都很大。對此類人員,有學者認為仍應依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但以非法經營罪處罰傳銷犯罪不僅不能體現罪名的區分功能,而且也不能揭示傳銷的本質,況且目前大量存在的“拉人頭”式傳銷只需繳納“入會費”就可獲得發展下線的資格,并不存在經營活動。同時非法經營罪的量刑高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量刑,如此定罪處罰,勢必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此問題的解決可借鑒日本1978年專門針對傳銷活動而頒布的《無限連鎖鏈防止法》,該法第六、七條分別規定了職業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罪以及一般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罪,并規定了相應的刑罰。因此,建議立法機關針對傳銷活動積極參加者增設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加傳銷組織罪,并設置輕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刑罰。此舉將有助于增強刑法自身結構的內在統一性。
健全網絡信息技術監管
打擊網絡傳銷必須依托網絡信息技術。2010年國家工商總局頒布的《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稱“辦法”)在創新網絡監管方式方面做了有益嘗試。例如,要求網絡交易平臺經營者要承擔對在其經營的網絡交易平臺上提供商品和服務的經營者及其發布的信息進行檢查監控的義務;將企業信用監管作為主要監管手段,要求工商系統建立健全網絡經營主體信用分類監管信息系統;要求以網絡信息技術為監管依托,適應網絡無地域限制的特征,實行工商系統內全國聯網一體化監管。上述制度對于打擊網絡傳銷犯罪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遺憾的是,該“辦法”僅是行政規章,法律位階過低,其制度優勢尚未得到應有發揮。執法實踐證明,打擊網絡傳銷犯罪單靠工商部門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鑒于國務院已經將《網絡零售管理條例》列入行政立法規劃,建議該條例在規范網絡零售活動的同時,還應認真總結近年來打擊網絡傳銷的正面經驗與負面教訓,建立健全包括工商、公安、工信、商務等機構在內的快捷高效、無縫對接的全國互聯網一體化合作監管機制,既強調各部門之間的明確分工,也要著眼于形成執法合力,從而更好地打擊和遏制網絡傳銷犯罪。
劉俊海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 博士生導師
尹紅強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